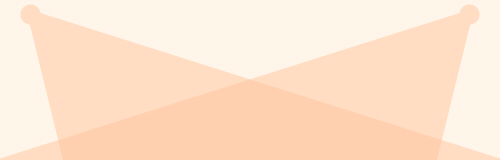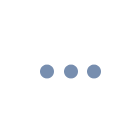推荐小说《小城祁阳》
小城,我回来了。
时间是某个秋天,他从南方踏上归途。许多年漂泊下来,他决定回去。
月台在昏黄的灯火中倒退,别了,广州。今夜我将离开你,今夜,我要回家。但我会思念你的。这座城市有着我深沉的眷念。他就这样想着,离开了广州。在那个秋天的深夜。
月台是游子的纪念,城市是某段旅行的纪念,带着纪念,他决定回去。
小城,是一座小县城,位于湘西南地区。湘江从小城的南边缓缓流过。他是祁阳,与小城共有着同样的名字。
火车穿过无边的黑暗,车厢里的人们面无表情,穿行在这条线上的旅人们,大多已经倦了。车顶的白炽灯残酷地照射出旅人们的颓态。
望着窗外的黑暗,他喃喃地念叨着两个字——小城。
小城的名字叫做祁阳。祁阳是他。小城是她。
小城也是她的名字,就是祁阳念叨着的那个名字,属于一个女人的名字。
小城,我回来了,你呢?你还是我记得的那个样子么?
他想起了小城。
时间同样是某个秋天。那天的下午并无太多特别。他正在吧台煮咖啡。香醇的曼特宁,在小城并不多见的咖啡馆里飘散出勾人的香醇。
那年他还年轻,岁月还未在他的眉头留下印记。青春阳光,正是花样年华。她就那样出现,手里拿着一份招聘宣传单。
这里招工吗?她问。
不招。他头也不抬地回答。
这传单上不是说要招工吗?她再问。
招男的,女的不要。咖啡的吸引力显然大过了这个问话的女孩。
为什么不招女的?
女的招满了,服务员已经够了。
我是来应聘吧台学徒的,我不做服务员。她继续说着,她似乎很想找一份工作。
吧台不要女的。他这次终于抬起了头,原因是手头上的咖啡已经煮好了。
长发,青春,并无半点修饰,自然,清爽,并不算漂亮,但看起来很舒服,颧骨饱满,眼神干净,这是个坚韧的女孩子。这是他对小城的第一印象。
你确定你要应征学徒?他没等女孩开口。
是的。女孩的回答很坚定。
很辛苦的。
我能做。
为什么?
我想学煮咖啡。
等等。他说着回过头去,然后走进了内吧的储物间,那里有台电话。他拨通了经理办公室的电话,好几分钟之后回到吧台。对长发女孩指了指旁边的楼梯间。上楼右转,经理办公室去填表。
这是他们的第一次接触。平淡无奇。后来,他们成了同事。也成了他的跟班。
火车呼啸,离小城越来越近了。他开始紧张起来,手心开始冒汗。他伸了伸手指,靠这车窗,他亲吻着无名指,那里有一枚小小的戒指。他却依然单身。当别人问他是否已经结婚,他总是笑而不语。笑的时候眼神里带着几许苦涩,脸颊开始浮现出两条很浅的法令纹。
七年,七年的时间,他的脸上开始出现法令纹。生活的长期不如意,失眠,不规律的作息,这些都令他看来总要比同龄人大了几分。七年,他已经三十岁了。那年他二十三,她十九。
他开始有些回避这次归家之旅。不止是小城让他觉得局促,还有家。家,在他的意识里已经淡漠了。与家人的隔阂早在许多年前就已产生。他想过要消融,却始终不得其法。
焦虑,不安,越是离家乡越近,越是心生胆怯。但终究已经踏上了这条归家的路,回头已是不再可能的事了。
火车继续奔驰,凌晨时间,他终于在迷糊中睡去,他的睡眠很浅,睡眠质量不好是他多年的积病,然而他并不承认这钟病。
模糊的视线里,高瘦的白衣少年,孤独地坐在一座坟前,那是爷爷的坟墓,旁边坐着他的狗——小白。月光清冷地照着这一人一狗一坟墓。那是一次离家出走。爷爷在时,是他坚强的依靠,爷爷走了,依然是他心灵的安慰。少年在低声抽泣,小白也在轻声呜咽。爷爷是他的,小白也是他的。清冷的月光也是他的……
给作者打赏
白戈
白戈一直很想写一个故事,纪念一些人和事,纪念一些值得眷念的城市。已经做了一年多的腹稿及准备,今天终于准备开笔。
这次跟往常不同,它将会是一个完整的故事,不会再因为别的缘故写一般就咔嚓。它会完成全稿。也许会写很久,也许很快,但无论如何,它会是一个完整的故事。
这个故事,有点边缘,有些颓废。思想,理想,价值观,这些都已在白戈的生命里成型,已无需亦无法更改,白戈就是这个样子。
“祁阳”是地名,也是人名。因为白戈是祁阳人,深爱着这片土地,虽然这里并不怎么好,甚至有些现象令人反感,但这无碍白戈对祁阳的眷念,无论身处何地。
“小城”也是一种纪念。她是白戈永远的苔丝·杜伯维尔。《苔丝》是白戈读的第一本外国文学,共她提起。曾经,她是苔丝·杜伯维尔,我是安琪儿·克莱尔。阿历克斯也真的出现了。但白戈却知道,自己从来不是安琪儿。他是真的苔丝,阿历克斯也是真的,唯独安琪儿不是真的。
不可否认,安琪儿是真的恋着苔丝的,但他却不够坚定。一定程度上,他是苔丝的悲剧故事里的一大帮凶。他的怯弱导致了苔丝最后的悲剧。
生活总是充满变故,她已不再是苔丝。但她又是苔丝,在我的映像里,她永远都是。
爱、安宁、纪念、追寻、线条、旅途、在路上、守候……
2011-05-22回复
白戈
再漫长的旅行都会有它的终点,当天大亮的时候,火车终于到站了。火车上的这一夜,他的睡眠质量显得更加惨淡。一脸倦容的他,跳下火车,月台上到处是人。下车的,上车的,挤作一团。他眉头轻皱,似乎有着许多不满。但终究是无济于事。
终于,人群散去,火车继续前行。一直到挤出火车站,他终于有点时间来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。这是家乡熟悉的气味。清晨的车站广场还未显得凌乱,空气也因为这一场夜而变得纯净。提着他的帆布旅行包,他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了进去。他的旅行包已经用了很久,很破旧,已经开始泛白,打了几处厚实的补丁。这趟旅程下来,又新增了一处破洞。是该补一补了。
旅馆的小房间里,破旧的帆布旅行包打开了。里面有几件换洗的衣服,有一些书,一些用来记事的本子,还有一台相机以及几件日用品。近年来,他一直做着各种旅行,用文字记录路上的点滴,拍一些并不常见的照片,然后卖给旅行杂志社以用作下次旅行的费用。有时他的经济状况并不太好,便会逗留某处,寻一些零工,等凑够前往下一站的路费,他便再次出发。一路旅行,一路写点文字,在一年以前,他写的一个剧本被来自北京的某青年导演接纳,借着这个机遇,又出了一本销量还算可以的书,被灌以草根作家的头衔。生活状况终于有所改善,但内心里的孤独,又该拿什么来慰籍?
他做过酒吧歌手,做过调酒师,做过排档勤杂工,做过餐馆服务生,甚至在工地做过小工。但每一份工作都做不长久。认识小城的时候他是一名咖啡师,那是他唯一做过的一份长期工作,一共做了十年,从学徒开始,一直到二十六岁,他不再从事这份工作。从那年起,他开始放弃原有的生活,开始旅行。他需要旅行,一场接一场的旅行。只有在路上,才是他的生活。
曾经有个朋友问过他,你是否就真的这样一直走下去?从没想过安定?
想过,但后来没有了。
为什么?
倦了。
一个简单的“倦了”,已经足够成为上路的理由。他决定上路,漫无目的地走。背负了太多、太久,他决定做简单的自己。
四年,旅馆还是这家旅馆。长达四年的旅行,就从他现在所住的旅馆出发。距离上次回来已经四年了。四年的时间已经足够改变许多。但这间旅馆没变,他也没变。靠马路的窗子依然能看到对面的早餐店正卖着米粉和油条。米粉汤泡油条,许久没试过这种味道了,四年了。
四年前的那个秋天,就如今天这样。他从车站里出来,然后在旅馆对面的早餐馆吃了份米粉加油条。身后放着两只很大的行李箱。一只是他的,还有一只是她的。
两只沉重的箱子,他从广州带回来的。他的箱子里面是书,她的箱子里面是塞紧的衣物和几条毛毯。它们的重量加起来达到了八十多斤。他就那样从广州的出租屋拖到了火车站,然后拖上火车,最后拖到了这里。后来,小城来了,带走了她的行李。
与小城同来的还有一个男人。男人帮着小城将行李放在一辆商务车的后备箱里,然后绝尘而去。再后来,他走了,今天,他回来了。
他依稀还记得小城临走前,眼神里的那种难以言说的复杂。说不清的滋味,说不清的余味。他还记得男人眼里的疑惑和拘束。
他并不认得男人,却已预知了故事的结局。茫然、无助、悔恨、愤怒、焦躁、不安,各种不良的情绪滋生蔓延,他觉得心慌。
这种心慌他曾有过一次经验。很久以前,他还是个少年。那时,他十五岁。那时候有小白陪着,还有爷爷。虽然爷爷已经不能再开口说话,但爷爷就在身边,他并不觉得恐惧。然后,小白死了,被人药死吃了。再然后,他离开了家,开始人生旅途的第一次长途旅行,在上海开始了他十年的咖啡师生活。一直到四年前,走向一个极端。
2011-05-22回复
白戈
认识素,是在回来小城后的第四天。白马小区的一个诊所。素白的手上挂着点滴,她坐在他的旁边。他的手上也挂着点滴。血脉膨胀,针管刺进他的手背的静脉血管,他的手指细长,一双好看的手。男人的手也可以很好看。他的右边脸颊贴了块纱布,殷虹的血将纱布浸染,边缘处可以看见已经凝固的黑色的血块。
诊所里的祁阳,正翻看一本书,莎士比亚的悲剧集。兴趣正浓的时候,点滴正好打完,橡胶管里开始回血,然而他并不知道。
这时她说话了,有点沙哑,她说:你的针打完了,回血了,医生,医生……
他只是抬头看了下正输液的手,不紧不慢地用另一只手将橡胶管上的活动阀门拧紧,然后等着医生来处理。回头看了眼坐在旁边的女子,点头微笑了一下以示感谢。
医生来了,很快处理完毕,换了瓶新的药水,交代了几句又去忙别的了。诊所门口的麻将桌正等着他回去出牌。
她说我好像见过你。我看到你跟人打架了,在罗口门。
他说:是吗?
是的,那天晚上你从罗口门那里过,手里提了个包。
我刚从外面回来。
一回来就打架,你不怕吗?知道那些是什么人吗?
他们是谁我不知道,我只知道,谁欺负我,我就绝对要还手。我为什么要怕?他们不过人多而已。
他们是外面混的,人很多。有一个是我初中同学,经常欺负人。
他不再说话。
回来的那天晚上,他照往常回祁阳一样,总要去罗口门的眼镜饺子馆吃碗红薯粉。他说那是地道的祁阳味道。高汤不错,酸豆角也很好,合他的胃口,切几片火腿,添两个鹌鹑蛋,加少许木耳。价格也公道。去南方以前,他经常来这里,跟小城一起。但现在只有他一个人来了。
离开的时候,在十字路口转角那里的烧烤摊前面,几个酒鬼神经质地咆哮。他厌恶地看了一眼。然后几个酒鬼为了在同行的几个年轻女子面前展示他们的威风,将他围了起来,要他敬酒道歉。他们说他看了烧烤摊前面的年轻女子,要他道歉。
他说这种货色的女子也只有你们这样的白痴才把她当宝。
事件由此从争执发展到斗殴。他踹倒了两个酒鬼,一拳打肿了一个酒鬼的眼睛,然后在逃跑的时候被一只飞来的破啤酒瓶划伤了脸颊。他捂着脸没命地跑,他知道,只要被那些酒鬼追上,他将至少躺上半个月的医院。好在酒鬼本身已经喝晕了,他安全地跑了。人民路边上的一个黑暗的小巷子里,他联系了他在小城祁阳的老友。脸颊生疼,但他任然慢条斯理地跟老友解释他的状况。
老友来了,带了一车的兄弟。老友也是小城道上的人物,手下带了一批小弟。老友的名字叫三公子,还算有些手段。只一个晚上就摆平了这次斗殴事件。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。只有他的脸上,贴上了一小块纱布。他住进了老友三公子在白马小区的一处房子。
你喜欢外国文学?诊所里坐他旁边的女子问他,声音沙哑。
他转过头去,点了点头,算作回答。
我也喜欢读外国文学,但是不喜欢悲剧。你叫什么名字?我叫许素。
祁阳。他的回答简短,清晰。他并不太愿意跟陌生的女子说话。
我知道这里是祁阳。
我姓祁,叫祁阳。
祁阳,还真有人叫祁阳的啊,你的名字挺有趣的。啊,我的针打完了,医生,医生……
那天晚上,他在老友的房子里,看着窗外的路灯,想起了白天认识的女子,许素。挺有意思的,他想。
他忽然想去看星星。旅行的时候他经常露天躺在某个高处,仰望天上的星星,感受自己的渺小。
秋高气爽,秋夜的星空格外的清晰。他庆幸自己在这个小城还能看得见天上的星星。广州的高楼阳台上也能看到星星,但太少太模糊。迷糊中,天上的星星连成一线,又变幻成各种图案,最后幻成了一张脸。小城?还是许素?他已无法分辩。或许谁也不是。
2011-05-24回复
白戈
当命运的轨迹沿着同一方向运行到某一程度的时候,往往会有一些意外发生。回到小城祁阳,他的人生道路终于又开始了另外一种形态的延续。他开始考虑是不是先留下来,在这个已经有点陌生的故乡小城生活一段时间。
这种想法的出现是在伤好了之后的一个下午。那天下午的太阳很好,金黄的阳光射过黄道门的街道。空气中漂浮着细小的颗粒。路边的小吃摊子滋滋第炸着臭豆腐,散发出很好闻的气味,和着阳光里的颗粒,这是小城特有的味道。
黄道门那里有一栋很旧的居民楼,小楼的三楼住这一位刺绣很好的中年妇女。她叫春嫂,能做一手好针线活。小城里许多人家找她刺绣。祁阳在这个下午,拎着他的破帆布旅行包出现在这里。他的包很旧,有些泛白,打了几处厚实的补丁,另外还有一个新近才破了的口子。春嫂能够帮他的破包打个很结实的补丁。
认识春嫂是小城还没有离开他的时候。他有一次去冷水滩参加一个职业培训,刚好赶上他过生日。小城到冷水滩来看他。在来时的路上,她新买的大衣被小偷划了个口子,就在左手边的口袋那里。好在东西并没有丢,但那个被刀子划出来的口子却极为显眼。
步步高超市的门口,她打电话给他。她说你现在在那里?
我在上课。
想我吗?今天你生日,生日快乐!
他走出培训教室的门,压低了声音说,想你,你却不在我身边。生日礼物准备好,我还三天结束培训。
想见我吗?
你来了?在哪?
不告诉你。
城,你真的来了?我现在就来找你。
步步高,等你,不准迟到,五分钟。
等我,不见不散。
他匆匆挂断电话,然后跟培训讲师撒了个谎请假离开了。他要去见他的情人。热恋时刻,情人间的相思胜过任何煎熬。
他看见了她。人来人往的街头,寒风肆掠,她不住地跺脚、搓手,为了取暖。她低头向手中呵出一口热气的时候,一双很好看的手包围了过来。带着一份温暖。她认得他的手。那双手曾手把手地教过她煮咖啡,教过她雕刻水果。
他将她拥进怀里,很用力地拥抱。他说,我们拥抱着就能互相取暖,我们依偎着,就是幸福。
她说你迟到了,请我吃东西。
步步高超市旁边一条避风的巷子口,那里有新疆人的烤羊肉串。她把手伸进他大衣的口袋,靠着他的肩,相互依偎着前行。口袋里的温暖从他的心口出发,温暖着她的冬天。与他一起,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
他发现了她口袋的裂缝,他担忧地捧着她的脸。这张脸干净透明,饱满的颧骨,晨星一样的眼睛闪闪发光。他吻了她的眼睑。 她的脸洋溢着幸福的羞红。
她不在乎,为了他,她愿意做很多事。她没有为他准备任何礼物。他说你就是我最好的礼物,你是上苍赐予我的最好的礼物。冷水滩的湘江桥上,他们放肆奔跑。青春烂漫的时光,在大桥上的牵手中无限蔓延。那是一个温暖的冬天。
回到小城祁阳后,他到处寻找好的裁缝,力求能帮她补好衣服上的刀口。从昭陵街到椒山服装市场,还有芦家甸的裁缝店。他问遍了所有的裁缝师傅,但看到他拿过来的衣服,最后都摇了摇头,表示自己无法修补。最后在他当时的房东老太太那里,他知道了春嫂这个人。
春嫂的手艺并不是虚吹出来的。淡黄色的金线在她的大衣口袋那里绣上了一朵蜿蜒秀丽的玫瑰。升展出来的线条,飘逸,优雅。完全看不出曾被锋利的尖刀割破的痕迹。
看着她兴奋的笑容,他像个半醉的呆子。那是他,还有她的幸福时刻。小城,祁阳。
多年不见的春嫂,如今已可以改叫大娘了。头发开始有些花白,岁月的沉淀,睿智,从容。年龄的增加并没能减少她的手艺纯熟度。帮他补好了补丁,她看了他一眼。然后她说,怎么一个人来的呢?女朋友呢?结婚了没有。
他说她嫁人了。眼神有些暗淡。他想不到春嫂还记得他和他的小城。
春嫂叹了口气,你们这些年轻人啊,太不珍惜了。多好的姑娘,多好的小伙子。怎么就……
春嫂没有再说下去。
是啊,多好的姑娘,怎么就这么嫁了别人呢?多好的恋人,多好的幸福时光。只是昨日黄花,今昔又是何年?
于是他突然间有个想留下来生活一段时间的念头。这里曾经有过他难以割舍的纪念。他说他已经一无所有,他说他还有很多……
2011-05-25回复
白戈
从春嫂那里出来,他碰见了一个人——许素。
老旧的楼梯转角,她突然出现。咦,你怎么在这里?你的伤好了吗?
早两天就好了,我来办点事。
你找春姨?我看你的包就知道了,一定是春姨补的。
他知道她说的春姨就是人们口中的春嫂。他点了点头,是的,我的包破了,来补补。
哦,这么旧了,怎么不换一个?
他不再说话,眉角轻微收缩,似乎不愿在这个话题上停留。他只点了下头说声我有事,先走了。然后匆忙离去。
回去的路上,三公子打来了电话,说回来这么久了,也没好好地给他接个风,前些日子有些麻烦事耽误了,今天晚上去故乡缘喝两盅。
故乡缘,故乡,陌生而亲切的名字。离开了许多年,故乡的许多事情已经模糊。有多久没有好好地看看这个生养自己的地方了?他突然决定先回家一趟。接风的事过两天再讲。他掏出手机,给三公子去了个电话,告诉他自己的决定。
电话那头,三公子表示理解,并催促他要回去就赶紧,晚了没车,在家好好玩几天。
熟悉的公路,熟悉的景致,意识里却模糊起来的家。上次回家是什么时候已经不大记得了,他只记得父母亲的头发已经开始花白。他想起上次出来的时候,父亲骑车送他。摩托车的后座上,可以看见父亲后脑已经开始泛白。有些心酸,想哭的冲动。但眼泪始终不曾留下。父亲送他到镇上的车站,父子对视了一眼,没有任何言语,挥手再见。父亲的眼里饱含歉意。离去的背影在秋天的太阳光下,有些细长,有些萧瑟。父亲老了,那是他那时心里的一声叹息。
在路上的很长一段时间里,他刻意去回避这种亲情冷漠下的荒凉。那是他不愿去面对的伤。但更多的夜里,星空下飘落的是对家的思念。他曾努力地去回忆少时的生活,试图寻找成长历程中难得一见的温情。
他记得十岁的时候,在山上玩,摔伤了背,导致内出血,鼻孔不停流血。越流越大,像极了杀猪的样子。血不停地冒,他觉得自己快要死了, 身体越来越轻,自己好像在天上不停地飞。意识渐渐模糊。后来,他听到父亲颤抖的声音,还有母亲带着哭腔的呼喊。他的眼角流下了泪水,父母亲终究还是爱着他的。那次,是他记忆里最深刻的一次关于父亲母亲对他的关爱。也只有这一次。当然这并不代表他们不爱他,只是平时这种爱并没表现出来或者用错了方法。
然后更多的记忆,是父母的争吵。他们从一件小事开始吵架,越吵越凶,然后母亲被打,父亲出走。他伸手想要抱抱母亲,试图给母亲一点安慰,结果等到了一个冰冷的巴掌。后来,他开始每天天黑才回家,开始逃避。他不想看到自己的父母任何一方受到伤害,但他却对这些无能为力。他还记得他去上海后没多久,父亲以打官司的借口骗了他一个月的工资,然后去了贵州,谁也不知道父亲究竟是去贵州做什么去了。他无法改变这个家庭的格局。再后来,他习惯了,习惯了这个家里的一切变故,渐渐变得麻木,也渐渐变得孤僻。他有自己的一个空间。
小时候,每天下午放学以后,他总在家后的山上躺在草地上仰望蓝天。那时候的天很蓝,很纯净,有白云悠悠飘过。他想变成一朵无拘无束的云,随意地飘往任何地方,只要不是呆在家里就好。爷爷经常在山上干活,发现了他的不安与孤僻。于是在更多的日子里,爷爷带着他一起干活。有时爷爷带他去锄地,种黄豆,种花生和玉米,一起砍柴。
爷爷还跟他讲很多的故事,讲老一辈传下来的各种传说,讲神话故事,讲过去的艰苦生活。他觉得很惬意。爷爷就是他的太阳。他的脸上渐渐回复了孩子该有的笑容。那样的生活一直持续了三年多的时间。那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三年。他到现在还记得他给爷爷搓烟丝的时候,爷爷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的样子。
与他一起的还有小白,他的狗,他忠实的伙伴。它是他唯一分享秘密的朋友。一只陪伴了他将近五年的狗。
爷爷在他初二的时候走了,小白也在他过了十五岁生日没多久就被药狗吃的人药死了。
长大后的许多年里,他渐渐明白了一些事理。明白了父母终究是父母,也明白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去恨他们。他试图改善家里的关系。他从上海回到了小城祁阳,定期回家。但是,多年的习惯,他已无太多的语言来与父母沟通。他不知道从何做起。父母似乎也已习惯了他的孤僻。与家人的关系就这样不冷不淡。这个家,真正能让他记挂的,只有弟弟。同样的,与弟弟之间也变得冷淡了许多,弟弟刚开始懂得一些事情的时候,他去了上海。幸好那时候他还有小城,回家的时候不至于太过冷清。每当他觉得疲惫的时候,小城是他唯一的安慰。
回家的路上,他突然感觉到了一种悲哀。习惯性的心理因素,他渐渐有了继续逃避的念头。但终究已经快三十岁了,已经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。回家,多年以后,终于要回家了。
2011-05-25回复
白戈
多少回梦回故里,感受宁静山村的安宁。家,是安宁的代言。然而更多的时候,她只在梦里出现。现实的情况是,家的距离总那么遥远。但累了的时候,家又是那么近。 这种忽远忽近的模糊,令他感觉苦恼。对于家,他有着某种渴望,又存在一些排斥。矛盾的综合。
汽车在镇上的车站停了下来。已是黄昏时分。步行回家的路上,夕阳刺着他的眼,眉头有汗滴下。含盐的泪水侵蚀他的眼睛,流下泪来。
天断黑的时候,他在家门口出现。新盖的房子,空气里弥漫着清新的气味。那是用他一年前的那笔稿费盖的房子,在村子通往镇上的路边。在弟弟的QQ空间里他见过,两层的红砖房,窗台一下的地方贴了白色的瓷砖。房子是新的,家呢?还是原来的那个样子吗?
两手空空,他呆立门前。母亲正在屋里忙碌。他喊了一声妈。母亲的身躯猛滴一颤,转过身来。头发花白,略微有些发福,脸上布满皱纹。眼里却充满惊喜。四年的时间,太长的一段日子。儿子也变得沧桑了许多。浓密的头发已经许久没有剪过,胡子拉渣,脸色有点儿发黑。
她认得这张脸,那是她的儿子,祁阳。他的眼睛也有些湿润。毕竟是母子,这中间的神秘联系是任何力量也无法剪断的。然而他们都在犹豫,许多年的隔阂,许多年的沟通不畅,虽然有爱,却依旧在停顿。
他不知道是怎么进的屋,一直到吃饭的时候,他还是有些发懵。脑袋似乎要炸裂开来,耳朵里也一直嗡嗡作响。无所适从的尴尬。
父亲倒了碗米酒,要他一起陪着。酒很香,饭菜也很不错。只是少了些言语。一问一答,父亲问,他答。
这些年去了哪里?
到处跑,走了大半个中国。
四年,也不回家看看,你妈老念叨你。
想过要回来,但总是……,我也不知道怎么说。
这次回来呆多久?还出去吗?你妈年纪大了。
母亲年纪大了,父亲年纪也大了,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?无论如何让,父母毕竟是父母。他开始流泪。许久不见的眼泪。沉默,激动而压抑。眼泪顺着脸颊,流过嘴角,滴在碗里。呼吸变得沉重。
父亲叹了口气。包含着太多的意味。追悔,内疚,自责,唏嘘。年轻时犯了许多过错,他觉得很对不住这个孩子。只是醒来得太晚,等他醒来的时候,祁阳已经在生活的历练中成型了自己的思想。父子的距离一直尴尬着。
他努力控制了一下情绪,干完了碗里的酒。然后一言不发滴离开了饭桌。他习惯了这样。父母亲也习惯了他的沉默。他们谁都明白这中间的缘故。但谁都没有更好的办法来修补。
在家里一共呆了一个星期。这期间他除了去爷爷那里拜祭了一次,没再去过任何地方。漂泊了这么些年,他已经不在适应这个小山村的生活。小的时候做过的农活,如今已经是件再陌生不过的事情了。家里也已经不再种田。
父亲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,只是太多的时候没有走上正确的道路。他的一手好字是当年父亲硬逼出来的。父亲的书法在小镇算的上是颇有名气,口才也非常的好。近几年来,跟人组了个师公班。在农村,逢上哪家老人离世,师公是免不了要请的。父亲跟了一个很有名的师傅,一年下来的收入还算可观。虽然师公这一行存在着许多争议,但在这小镇里面,倒还算是个好行当。同时父亲还兼做礼生,城里叫司仪。母亲在家里开了个小杂货铺,日子也还算悠闲。每到下午闲的时候,跟隔壁邻居一起打打小牌,搓搓麻将。家里的日子总算安稳了些。
从爷爷那里拜祭回来的那天晚上,他告诉父母,自己决定留在小城生活,写点文字。他已经不想再做任何工作,先写写文章看能不能继续发展,实在不行在做点小生意,也算对自己的生活有个交代。
这次依然是父亲骑车送他出来。后座上的他,再次见着了父亲脑后的白发。比起四年前,越发的苍老。父亲回程的背影也比四年前更加的萧索。开往小城的车上,他再次决定了留在小城生活的决心。改善这个家庭的状况,虽然需要时间,但总是要去做的。家,渐渐清晰起来。
2011-05-26回复
白戈
故乡缘酒楼,小城口碑最好的一家酒楼。祁阳从家里回到小城。这个晚上,三公子在这里为他接风。同来的还有胖子。胖子是他的朋友,也是三公子的朋友。他们一起走过了一段并不算长但深刻的路。
胖子并不胖,甚至很瘦。1.75米的身高,只有110斤的体重。很难想象这么瘦的一个人却叫做胖子。据胖子自己讲,他曾经很胖,后来躺了次医院,就再也胖不回去了。胖子的声线很好,有一把好嗓子,曾经想过要去参加湖南卫视的选秀节目。但不知道什么原因,临行前取消了那次选秀行动。如今胖子跟人合伙开了个婚庆公司,专职做婚庆主持人,在小城颇有名气。
他们的相识是在一列通往上海的火车上。三个意气风发的少年,因为说着同样的方言,彼此成了朋友。有人说,火车上的旅行是一场艳遇,彼此陌生的两个人,很可能在下车之前留下自己的电话。那年春节后的火车,成就了一段铁三角的传奇。
那年的整个春天,除了他,三公子和胖子的生活并不如意。他刚从学徒升格成为吧师,一千的月薪虽然解决不了什么问题,但保持最低的温饱还是可行的。
当那种艰难的无力感积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,三公子带着胖子一起爆发了。他们加入了一伙地下势力,连带着他也开始跟这个见不得光的世界有了接触。在那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,有过血腥的厮杀,有过深恶痛绝的背叛,有过惶惶不可终日的逃亡……
他还记得三公子在胖子的搀扶下满身是血的敲开三人合租房的门。三公子被派去参加一场群殴,胖子也在其中。午夜的漆黑巷子,连天的喊杀声,这一仗,他们输了。逃回来的时候三公子已经奄奄一息。胖子也受伤不轻。三公子足足躺了三天,才悠悠醒转,若不是祁阳冒着风险找了个黑诊所的医生,也许现在坐在这里的,只有他跟胖子两个人。患难见真情,他们养伤的日子里,他成了他们的全职保姆兼门卫保安。连续的旷工终于令他丢掉了工作。
当他们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之后,他们一起回到了小城。经受住了死神的考验,三公子的眼神变的阴沉起来,心也变得更狠。后来他终于在小城建立了自己的势力,成为道上有名的一号人物。
胖子则迷失了很长一段时间。他开始酗酒,玩女人,赌博,种种不良嗜好占据他的生活,他变得颓废。后来无意间发现他很有唱歌的天赋,并且自学成才,弹得一手好吉他。刚好三公子跟人合伙开了个酒吧,于是他成为了酒吧的驻唱歌手。再后来他发现了唱歌的乐趣,可以赚取可观的生活费,还能借职业之便引诱各种意志力薄弱的女人。他还有个外号叫花公子。 当他的歌手事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,有人看中了他的口才,让他以干股的形式一起组建了婚庆公司。有业务的时候他就回来做婚庆司仪,没有业务的时候就继续他的歌手生涯。
祁阳回来之后,正好本地第一家咖啡馆筹备开铺,于是他做起了本行。三公子曾不止一次地邀他入伙做大事。他一直很坚定自己要做一名咖啡师的想法。上海的生活,似乎每天都在亡命,咖啡成了他生活的调节器。而且因为咖啡的缘故,有拥有了一次似有若无的初恋。虽然短暂,但很美。咖啡成了他生命里的一份子,他愿意为了这份职业付出他全部的精力。
小城也在他进入这家咖啡馆之后没多久就进入了他的生活。生活开始改变,不再冰冷,不再生硬,有了爱的温度。
故乡缘的包厢里,他们喝了很多酒。三个人,三箱啤酒。许久不曾这样醉过。喝下去的,不仅是酒,还有青春,还有一起的疯狂岁月。每一滴酒都是一个故事,属于他们三个人的故事,铁三角的传奇。无论生活怎么改变,无论际遇如何变幻,沉淀在岁月里的友谊恒久、坚定,直到永远。
他们喝酒,唱歌。发疯一样地笑。他们唱友情岁月。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,彷佛想不起再面对,流浪日子你在伴随,有缘再聚。他们唱海阔天空,唱青春舞曲……
小城的深夜,灯火暗淡,空中飘来阵阵歌声。他们手舞足蹈地唱着、跳着。唱到天色发白,唱到天昏地暗,唱到失声狂笑,最后唱到流下眼泪。许久不见的眼泪。
2011-05-27回复